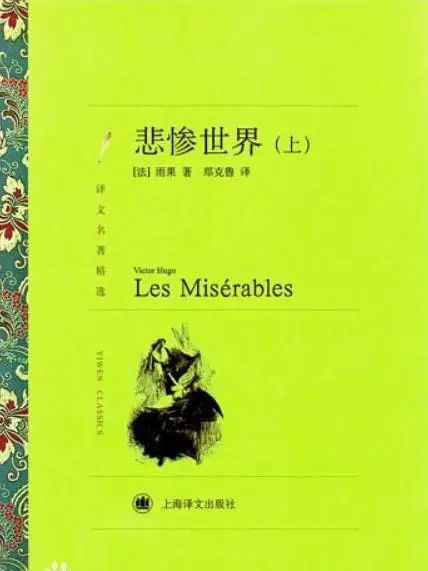许多人知道郑克鲁的名字,是通过《家族复仇》《基度山恩仇记》《茶花女》《悲惨世界》《巴尔扎克短篇小说选》《法国抒情诗选》等法国文学作品。昨晚10点,翻译家、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郑克鲁在医院去世,享年81岁。 郑克鲁是在翻译、教学和研究三大领域同时取得不凡成就的翻译家之一。其实,那些耳熟能详的书都是他在研究和教学之余翻译出版的。他对于法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研究探讨,完全基于一手材料的直接阅读与领悟,将翻译实践与学术研究同步进行,并相得益彰。 郑克鲁出生在澳门,四五岁时离家。仿佛是铭刻在血液中的对西方文明与外来文化的敏感与探究,让他命中注定般走上了文学翻译这一中西交流之路。他翻译的第一部雨果作品就是《悲惨世界》。2012年,因为出色翻译法国著名思想家、文学家西蒙·波伏瓦的代表作《第二性》,郑克鲁获傅雷翻译出版奖,这个奖是对他半生翻译工作的褒奖。 郑克鲁主编的《面向二十一世纪教材——外国文学史》是学生们普遍使用的教材,他主编的《法国文学史》《法国诗歌史》等也有很大影响。他在上海师范大学出任中文系主任时打造的“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”专业,至今还是国内同类专业中的佼佼者。 郑克鲁译《悲惨世界》 网络图 2008年,郑克鲁还翻译了法国作家、法国最早的一代飞行员之一圣埃克苏佩里的作品《小王子》,由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。 他说自己没有什么爱好,翻译就是他的爱好。 “做一个译者绝不是易事,还需要自己的刻苦努力。”这是郑克鲁常常对后来者说的。“翻译文学作品,是一项艰难的工作,其中诗歌的翻译难度最高。而翻译小说,也不是单纯把一字一句译好就行,是要看整体。一部像《悲惨世界》这样几十万字的小说,我作为译者,绝不敢说自己译得毫无疏漏。”郑克鲁说。他强调译者良好的中文素养,“读者经常用来判定翻译好坏的标准,是看这个译本的文笔流畅不流畅、有没有文采。其实流畅是比较容易做到的,但如果都只是翻译成‘白开水’似的大白话,没有人会说你翻译得好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喜欢傅雷的译文,因为有文采。所以,译者需要有很好的中文素养,能够使用一些非日常用词,甚至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词。只要译者用得好,就能把这些词藻用‘活’。”(新民晚报记者 徐翌晟) 马信芳:郑克鲁,在翻译中找到乐趣 2018年6月15日,新民晚报“金色池塘”刊发《郑克鲁,在翻译中找到乐趣》,今与读者分享,以示缅怀。 2018年4月,新出版的38卷《郑克鲁文集》发布会暨郑克鲁学术与翻译思想研讨会举行。身穿黑色西装和粉色衬衫的郑克鲁脸色红润、神采奕奕。我问他如何看待退休生活,郑先生答道:“我在翻译中找到乐趣,因此才不辞辛劳,特别是退休后,依然一本接一本地翻译。” 在郑克鲁60年的翻译学术生涯中,已完成了1700万字文学翻译,近2000万字著作和编著,面对这样的累累硕果,我不由说:“今年正逢你的八十大寿。”“对,所以这38卷文集,是最好的礼物。”说到这里,他开怀地大笑起来。 从翻译家到研究学者 郑克鲁出生于1939年,其曾祖父是晚清启蒙思想家、曾写过《盛世危言》的郑观应。中学时,郑克鲁就酷爱文学,尤其对俄罗斯和法国小说情有独钟。报考大学时,本打算报考北京大学俄语系,不巧的是1957年俄语专业不招生,他报考了法语专业,从此与法国文学结下不解之缘。 郑克鲁觉得他很幸运。毕业后供职于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,师从李健吾先生。李先生要求他从扎扎实实的材料中求取真知,并要有自己的真知灼见。所以,郑克鲁在学术研究中特别注重搜集材料,从而有了自己独特的研究观。 当时的外文组组长卞之琳先生是他的“顶头上司”,卞先生建议他也要搞一点当代文学。这对郑克鲁来说,是个鞭策,他由此开始关注当代文学的动态,后来又系统地加以研究,这为他后来从事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打下了基础。 在外文所期间,郑克鲁看完了法文版巴尔扎克《人间喜剧》百分之九十的作品。他的翻译处女作是巴尔扎克的短篇《长寿药水》。接着又连续翻译了好几篇巴尔扎克的作品。1981年,他的第一本译作《家庭复仇》出版了。 《蒂博一家》是193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杜·伽尔一生心血的结晶,郑克鲁于1981年前完成了《蒂博一家》第一卷的翻译,五年内出齐了四卷。译作不仅得到了业界的肯定,1987年法国文化部向他颁发了文化教育一级勋章。 1981年至1983年,郑克鲁作为访问学者来到法国。回国时带回的众多书籍中,包含了一大批诗歌作品,译诗成了他的新爱好。1987年,他回到申城进入上海师范大学任教,从此开始了有计划地翻译法语诗歌,结集为三卷本《法国诗选》出版;后来又撰写了《法国诗歌史》。 郑克鲁写的《现代法国小说史》全面详尽地论述了20世纪的法国小说,而且分门别类,弥补了国内空白。正是在这两部著作以及对其他作家研究基础上,他又撰写出版了137万字的《法国文学史》。 还原“原汁原味”的波伏瓦 《第二性》是法国著名作家西蒙娜·德·波伏瓦的最重要作品,甚至被尊为西方妇女的“圣经”,先后被译成英语等17种文字。作为法国文学研究专家,郑克鲁对此当然十分熟悉。他说,就波伏瓦一生著作而言,其最重要的作品就是《第二性》,此书影响深远,光公开发表的论文就有约2.7万篇。但它却迟迟未进入中国,此书出版后的17年,中国台湾出了《第二性》第二卷的译本,而大陆的节译本出现在31年以后。 《第二性》所引用的材料丰富翔实,论证相当严密。波伏瓦博览群书,学识渊博,她的生物学知识达到了专业水平,她对马克思、恩格斯的有关著作也相当熟悉,她深谙人类学家关于原始社会的著述,而且涉及生物学、精神分析学、哲学、历史学、人类学、宗教、心理学、文学、法律、社会学等众多学科,特别是第一卷有“很多理论词汇”,专门术语充满了艰深,法文原版长达1071页,译成汉字约有70万字。郑克鲁经受了考验,靠着他的学识和素养,用了整整两年时间终于译完了全书。 功夫不负有心人,2012年,郑克鲁凭借其译作《第二性》(上下卷)从入围的十部大作中脱颖而出,一举夺得了第四届傅雷翻译出版奖。 重译总要比前人译得好 “我的研究与翻译道路是机遇与努力交织的结果。”谈起自己的治学与翻译,郑克鲁相当淡然,“在研究所里,研究工作是本行,翻译不算成果,然而我喜欢翻译。”所以退休之后,郑克鲁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翻译上,“以往的有些译本不是尽善尽美的,有些译本有不少错误,读者的阅读兴趣也一直在改变,这给了我重译经典的机会。如《基督山恩仇记》《茶花女》《悲惨世界》等。” “当然,如果是重译,总要比前人译得好些吧,否则为何要你做重复劳动?”郑克鲁说,“其实重译并不轻松,因为有了老译本,读者自然会比较,有比较就有鉴别。因此,每个句子我都要斟酌再三,既要准确,又要通畅,并力求文字优美,即所谓‘雅’。我的重译,一是力求做到准确,将前人的错译纠正过来;二是在文字上要翻译得流畅,尽量给人美的享受,让人觉得确是一个新译本。” 郑克鲁的翻译观念从一开始想挑选还未曾译过的好作品,逐渐发展到翻译有广泛读者的作品,然后又发展到主要翻译一流作品。因为随着年事渐高,他觉得时间紧迫,不能随便翻译。 在38卷《郑克鲁文集》中,收录有郑译的《悲惨世界》《巴黎圣母院》《九三年》《笑面人》等雨果主要作品。“剩下的字数不算太多,我决意全部译出,将来出一套《雨果小说全集》。”这是郑克鲁未来为之耕耘的新目标。